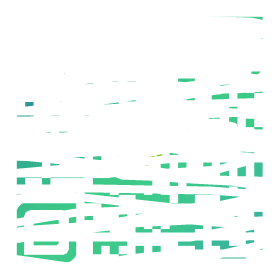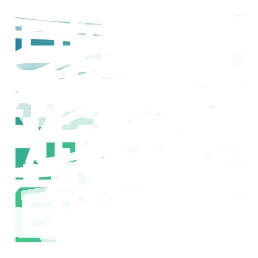前些天,楼下的住户装修,在过道上丢出了些纸盒。下楼的时候我看着一只黑猫从盒内一跃而过,便生出了一个主意,我想把自己装进一个箱子里。
我把这种事情叫做躲猫猫,我时常觉得自己的房间不够黑,所以每晚总会把眼罩带上摘下,想着办法堵住那些跑进来的光。凌晨的时候我与广场上一个souler抱怨自己的房间太亮,他便对我说他怕黑,他必须要整宿开灯才能入睡。我笑了笑,拍了房间周遭的漆黑,他无语般回我这都伸手不见五指,哪来的光。
第一次塞进行李箱里时候,是十几年前与父亲外出,他为了省下车钱便给我塞进了箱子里,在车上颠簸中头一次体会了盲人世界;工作之后,跟朋友合租,明白安静这个词的重要性,偶尔大晚上崩溃至极,便就着枕头缩进了床前的柜子里,那里的隔音效果比门要好得多;再后来便是跟前任在一块儿,那时候他总是玩游戏到深夜,我幼稚的以为藏了起来他会惶恐担忧,便蜷缩在洗衣机里。那个晚上我听到他起来上厕,唯独没有寻我。
我一直在与自己玩这种把戏,往一个箱子里面填满自己,缩成在母胎的形状。菲儿来找我时,我碰巧从盒子里一跃而出,她看着我古里古怪的行为,便打趣拿着桌上台灯,扬言要用手机记录我像极鬼的这一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