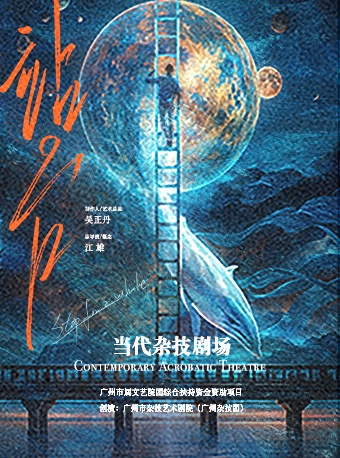回忆是座走不出的迷宫,每个转角都竖立着未兑现的承诺
回忆是座走不出的迷宫,每个转角都竖立着未兑现的承诺
我们会不会在出站口相遇

前言:跟@🍋神虎叔叔老弟学了《远去的列车》这首歌,唱着唱着就出了画面,不止是陈江河与骆玉珠在站台重逢,还有形形色色的人在站台演绎相聚离别的瞬间。因为我也是常候车的站台旅人。 《铁轨上的相逢与余温》文/半山客 雪粒撞上铁轨的瞬间便化作泪痕,在暮色里蜿蜒成银亮的河。我常站在这样的站台,看蒸汽在冷空气里凝成白雾。我数过十二趟列车的轮毂碾过同一道裂缝,看它从发丝般的细纹裂成掌心纹路般的沟壑。那个总穿藏蓝工装的老扳道工说,这道裂痕下埋着半块玉佩——二十年前某个暴雨夜,追车的男人摔倒在铁轨间,玉坠磕碎的脆响比霹雳的雷声更惊心。 站台西角的木椅上永远坐着一位织毛衣的老妪。灰白毛线团滚进过无数旅人的行囊,她却从不阻拦。直到某个雪夜,穿皮夹克的年轻人将毛线头系在行李箱上,红围巾在风里飘成一道割裂暮色的刀光,她才颤巍巍掏出把铜钥匙:"当年他留下话,等毛线织完第七件毛衣,就去第三候车室的寄存柜..." 话未说完,十几年未启的柜门轰然洞开,霉味裹着褪色的千纸鹤扑向月光。 列车进站时的轰鸣常让我想起山洪。相似的摧枯拉朽,相似的裹挟而去。月台上的送别者被汽笛声削成单薄的剪影,挥动的手臂渐渐模糊成站台上的灰点。我见过最漫长的拥抱发生在凌晨三点。穿貂皮大衣的女人死死攥着民工沾满水泥灰的衣角,指甲缝里渗出血丝。男人肩上扛着印有"义乌"字样的蛇皮袋,袋口探出半截褪色的拨浪鼓。"等我有资本装满两百个这袋子,我就回来开间玩具铺。" 汽笛响起时,女人将冻红的耳垂贴在男人胸前的玉观音上,冰凉的吊坠竟焐出一小片水雾。 站台最懂时间的慈悲。它见过太多抱头痛哭的离别,也见过太多欲语还休的重逢。那些以为刻骨铭心的伤痕,终会被车轮与脚步打磨上温润的包浆。卖茶叶蛋的妇人总在煤炉边摆个搪瓷缸,过路人可以往里扔枚硬币换勺热汤。某个冬至清晨,戴金丝眼镜的男人在缸底摸到枚缠着红绳的铜扣,突然蹲在地上泣不成声。八年前某个离别的黎明,他用这枚从中山装上揪下的扣子,换走了少女辫梢系着的红头绳。 最动人的告别往往没有声音。穿碎花棉袄的女孩每天黄昏都来喂流浪猫,直到某天抱着纸箱的少年蹲在她常蹲的角落。他们用火腿肠摆出北斗七星的形状,看野猫将星光叼进暮色。当北上的列车载走少年时,女孩在月台砖缝里种下七粒猫粮,来年春天竟抽出嫩绿的小苗。 暮色中的信号灯开始闪烁,像悬在尘世的第三个月亮。穿羊皮袄的老扳道工佝偻着背,把锈迹斑斑的道岔推向另一个可能。扳道房的老周头有本牛皮册子,贴着半个世纪的车票存根。1983年那页夹着张泛黄的结婚证,证件照上的铁轨穿透相纸,将新人分隔在虚线两侧。"她跟着支边列车去了新疆,我守着道岔等成雪人。" 去年春天有拄拐的老太太颤巍巍寻来,从提包里抖落出半本同样的册子——那些缺失的车票,正严丝合缝地嵌在老周头的记忆里。“现在,我倒是随时可以去看她了” 暮色降临时,铁轨会变成流淌的河。碎玉般的雪光中,我看见无数身影在汽笛声里相撞又离散。穿胶鞋的脚与锃亮的皮鞋交替踏过同一块地砖,蛇皮袋与真皮包在长椅上投下相似的阴影。某个瞬间,所有离别与重逢都坍缩成钢轨接缝处的火花——短暂得来不及许愿,却足够点亮某个异乡客衣袋里珍藏的家乡泥土。 我在渐浓的夜色里拢了拢围巾。雪又下大了,盖住新添的辙痕,却盖不住钢轨温热的脉搏。远处传来列车隐约的嘶鸣,像春雷滚过冻土——毕竟再厚的积雪,也困不住就要抽芽的春天。巡道工的油灯扫过栅栏时,照见半枚玉佩正在裂缝中泛着温润的光。或许再过二十年,这道裂痕会蔓延成相逢的轨迹,而此刻的离别,不过是人生延伸向黎明的必经之路,就像这延伸的轨道。
旅途的风景总是那么美好,哪怕只是站台的一瞬间。🚄✨





原创诗-站台🚉
站口太多了,我俩不在一个站口出来,
长长的站台! 漫长的等待!


往前翻了几期视频发现赵哥也听royster lee[感动]


结束了 收获满满的一天 打了个喷嚏 哪个哈儿在想我 ˊ˘ˋ*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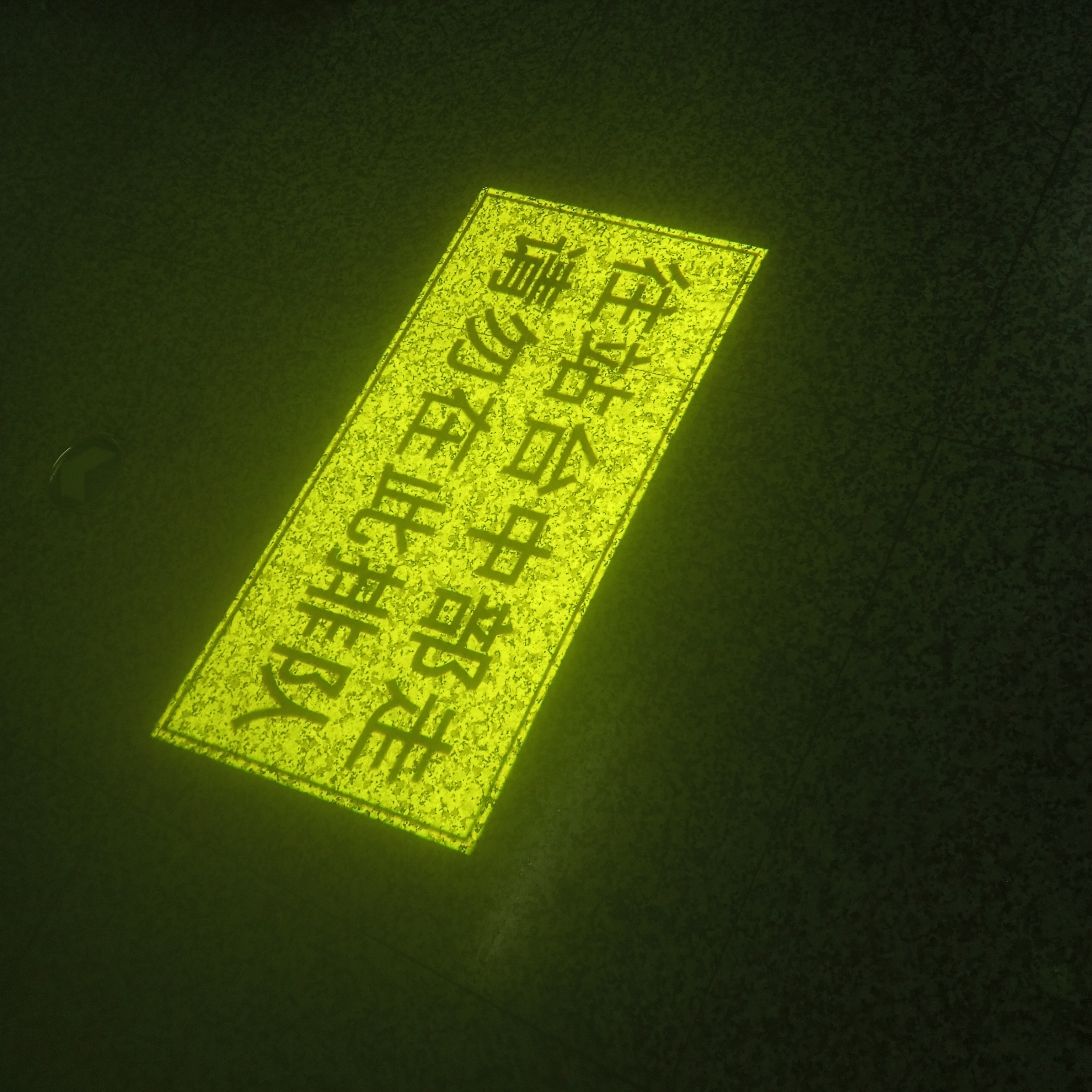


站台的故事,总让人有些感伤。希望我们都能笑着说再见[可爱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