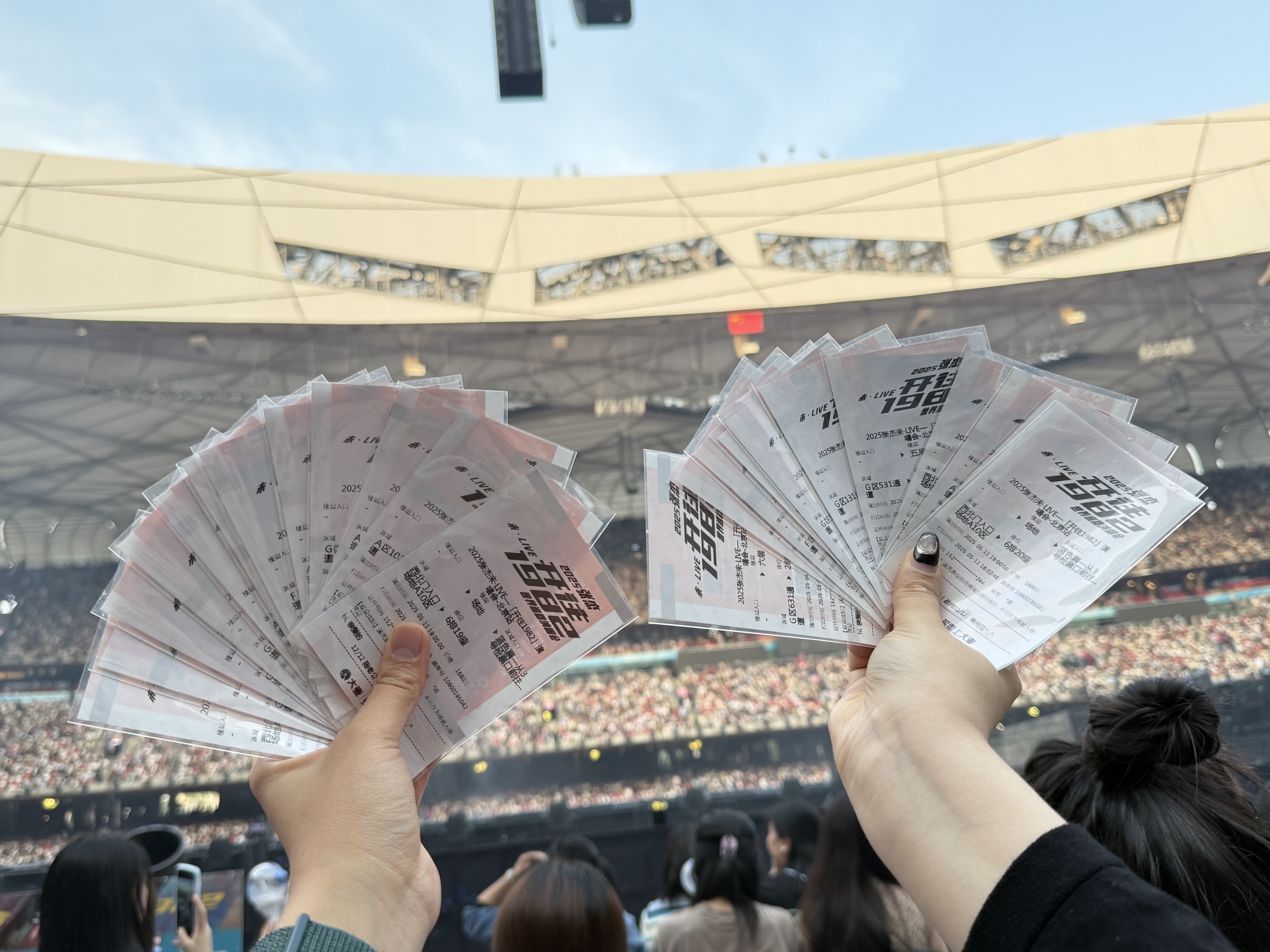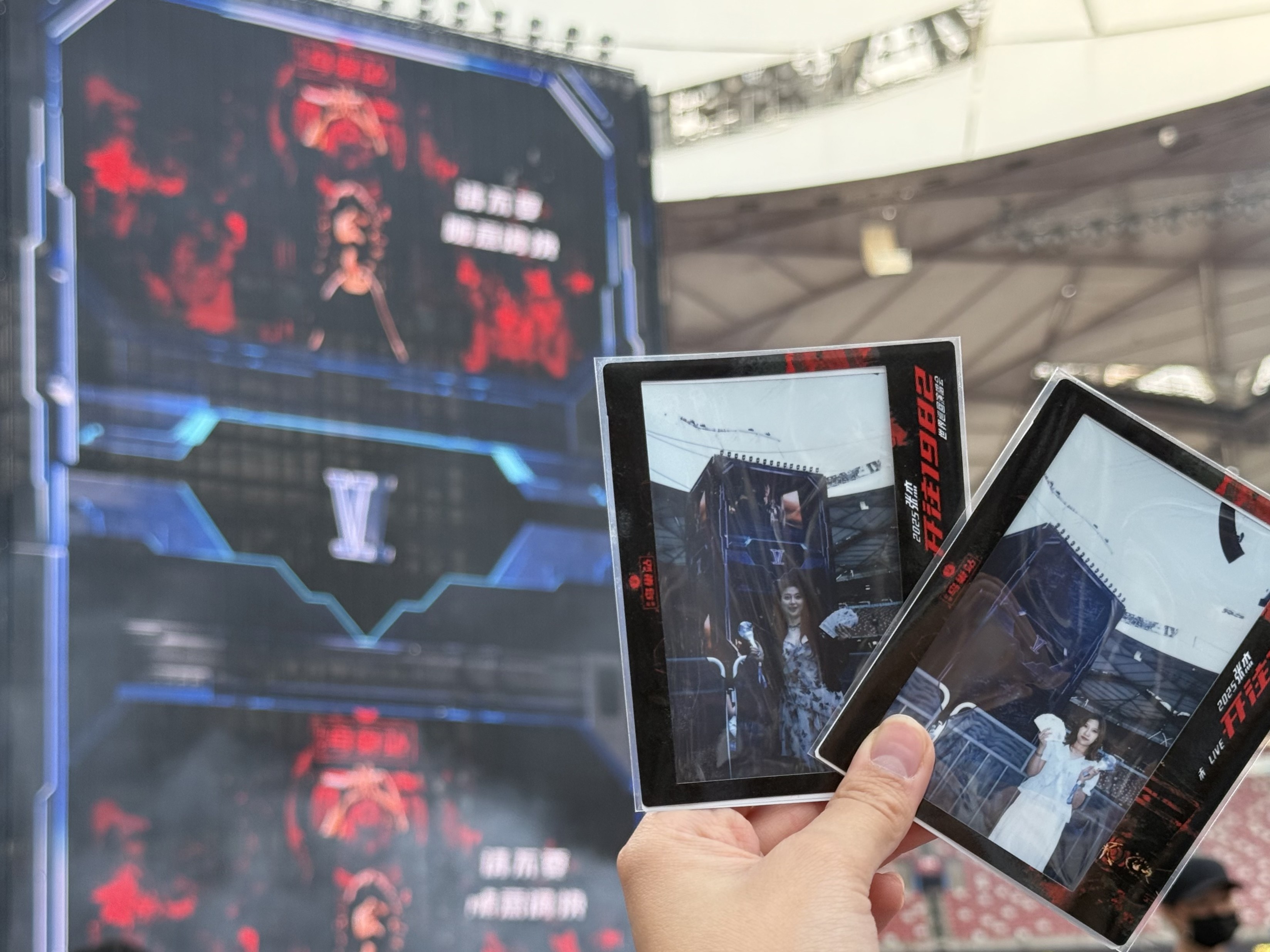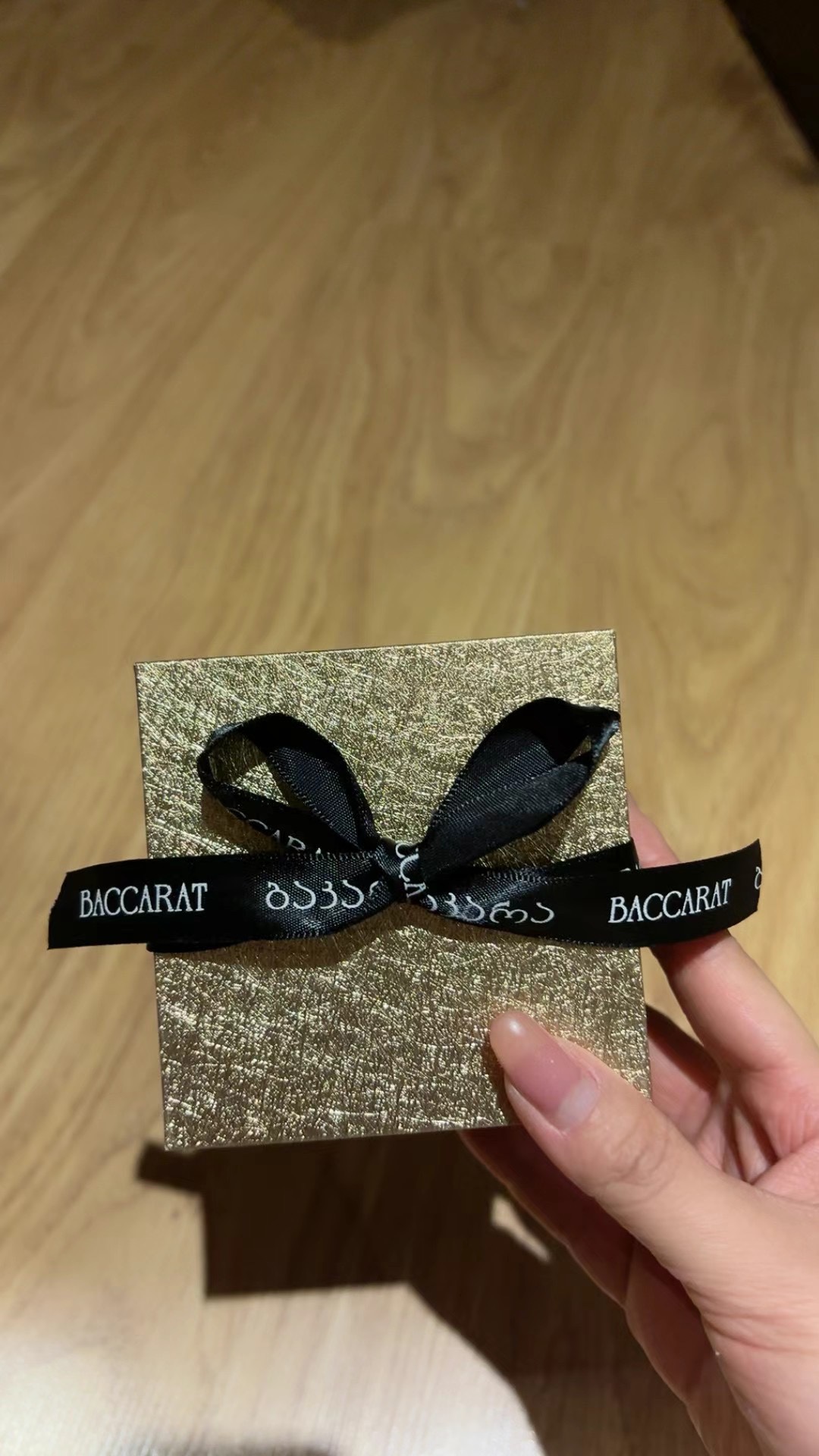用户:找对象(闪婚)
2025-05-19 19:10:31 晴
#幸福具象化的时刻 #结婚测评 #博罗人坐标惠州市 惠城区,博罗人,未婚,90年天秤,身高156,体重105,有车无房,性格时而内敛,时而逗比,五官端正,三观更正,通情达理,确定关系后感情是专一的。
文职工作,🤣其实我是一个很佛系的人,偶尔赚点外快就好开心,偶尔会去打打羽毛球。
我希望你是170左右身高,一个三观端正,阳光,处事成熟,有主见,不嫖不赌不烟,对感情专一的人,还有可以打征信报告和体检的。
私聊先自我介绍,包括年龄身高,工作和经济情况,爱好,和对未来的规划,期待双向奔赴
目标:1.不交友只找对象,半年结婚,人品靠谱,闪婚也可能。 唉呀,头发都等白了,死鬼还不滚出来[尬][尬]
自我介绍后 私聊可发照片认识
资料属实 >>阅读更多
用户:You包er
2025-05-20 22:54:01 晴
#你最想回到几岁 假如可以 我也想时光倒流[摸摸] >>阅读更多

用户:小言同学
2025-05-16 18:33:14 晴
所以不管是谈恋爱还是结婚的,男生都会有目的性的去获得一些东西(肉体或者金钱等)只要有所付出,就会想办法从女生身上获取,来弥补他的付出,权衡利弊#恋爱中男女的思维差异 #男女不同的爱情观 #说说你的爱情观 >>阅读更多
用户:饱了么
2025-05-20 00:08:38 晴
男人一旦有点钱,就开始不安分了,首先开始在网上搞暧昧???#好男人各有各的样渣男都一个样 #如何一眼识别生活中的渣男 [耸肩] >>阅读更多
用户:阳光暖宝
2025-05-19 12:42:57 晴
陪妈沫出片的一天
#藏在妈妈照片里的故事 >>阅读更多


用户:安于心
2025-05-20 13:44:36 晴
我好奇生理性喜欢和心理性喜欢是什么意思?两者区别是什么?#生理性喜欢是什么? >>阅读更多
用户:吃不饱
2025-05-15 00:34:19 晴
#生活哪有不疯的 #恋爱自画像 #半熟恋人 #2025脱单计划 本人28!!!有认真处对象的吗奔着结婚~玩玩的就别来了 >>阅读更多
用户:谢谢你的关注
2025-05-21 06:27:58 晴
#你最想回到几岁 岁月从不败美人[粉红心心] >>阅读更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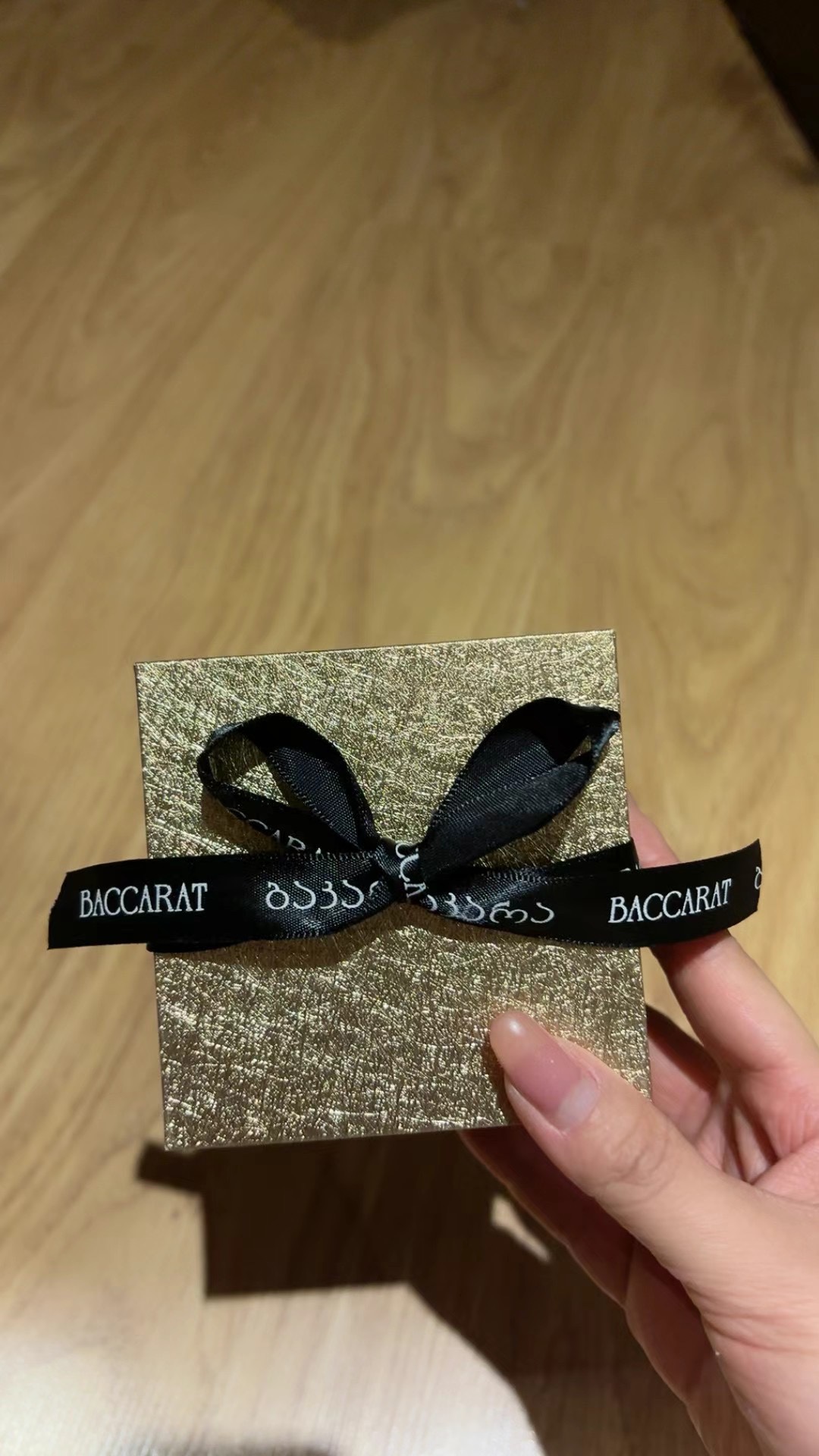
用户:🍊🍊
2025-05-20 10:19:42 晴
#我的情感故事 #我的情感故事 相亲,本人身高181,体重140斤,30岁,自己创业平时时间挺多,双子座,年收入40w以上,我做菜嘎嘎好吃,性格好话多,脾气也好,,衡阳3套房,找个160以上,90到00的,不能太胖身材匀称,不搞异地恋,不喜欢冷暴力,随时可以见见面喝喝下午茶认识一下,文明聊天不要和我聊虎狼之词什么借钱的,什么拖就别来打扰了 >>阅读更多
用户:司翎的碎碎念
2025-05-18 02:54:37 晴
朋友晚上打电话来哭诉,说自己相恋七年的男友背着自己偷偷去相亲,看中了一个女生毅然决然的和她分手并给了相亲女生18.8W的彩礼。而她想要8.8的彩礼男方却始终沉默……
我真的想不通,为什么有的人宁愿把高额彩礼给相亲对象,却不愿意给恋爱多年女友?#婚姻#结婚该给彩礼吗 #关于彩礼 >>阅读更多
用户:七月
2025-05-16 12:54:08 晴
在单位健身房慢跑,只想放松下僵硬的肩膀。同事暴汗如雨,我却只是微微冒汗,像一场敷衍的仪式。
耳机里随机跳到孟庭苇的《一个爱上浪漫的人》,旋律一起,让我整个人平静下来,想起过往,想起那年在台湾,静静发呆!外面下着雨。
切到下一首,竟是《第一滴泪》。前奏刚响就慌忙按停,像被烫到。这首歌的每个字都是往心里扎的针,如今旋律还是不敢碰。 一听就泪奔。你还是那个傻女人!!
时隔多年, 那天他忽然来电,号码没存,但那声“喂”像块烧红的炭烙在耳膜上。他说后悔、后悔,问还能回去吗!出来见上一面吧。我想他想见他,但我拒绝了,因为我怕自己失态,只要不见面,我可以一直强装下去。
他沉默很久,我说不必了。挂断后才发觉掌心全是汗,和现在一样。
这世界总有爱在伤口上撒旋律。#浅问一个问题 >>阅读更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