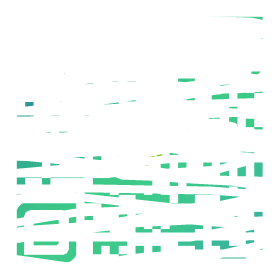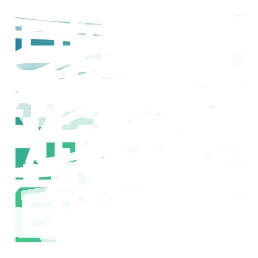前言:从老家返回北京的家里,打开背包时,母亲偷塞进来的一袋酸菜丝,让我瞬间破防。柳永《雨霖铃》中的离情别绪充塞心胸,原来在“宋词之外”,超越了具体时空的离别之苦,是人类共有的生命体验……不管古今。
《雨霖铃宋词之外》
暮春的京华浸泡在灰蒙蒙的雾里,像一块洇湿的宋锦。我伏在落地窗前,耳机里淌着《宋词之外》的戏腔,母亲电话里那句“你爸坟前的野山樱又开了”突然撞进耳膜。千里之外,寒蝉未起,而柳七的句子早已在喉间凝噎:“念去去,千里烟波,暮霭沉沉楚天阔。”
提前祭扫归乡时,老宅的窗扉仍浸着父亲初离世时的清冷。母亲执意要独自擦拭供桌,她佝偻的脊背在檀香里弯成半阙《雨霖铃》。我像小时候一样站在她身后数着她的白发,恍若看见二十年前离家的那个清晨——她将腌好的辣酱塞进我行囊,指甲缝里沾着暗红的辣椒粉。那时她尚有乌发可绾同心结,而今廊下的胭脂梅开了又谢,只剩“执手相看泪眼,竟无语凝噎”。
离乡的列车碾过子时的月光,母亲立在月台的身影渐渐瘦成一根断弦。耳机里的京剧韵白陡然拔高:“日日思卿,夜夜思卿”,铁轨的震颤中,我忽然读懂她为何拒绝北迁——父亲的魂还在老屋檐角悬着,她若离了这座浸透旧事的城,怕是连梦里都寻不见那袭泛黄的绿军装。
长安街的霓虹在雨幕里洇成一片醉妆,我常错觉母亲就坐在副驾座上。等红灯时转头,只瞥见玻璃上自己的倒影与柳永的残句重叠:“此去经年,应是良辰好景虚设”。车载广播里有人唱“雪中的花似一首无人堪摘的宋词”,我想起视频通话时,母亲总把镜头对准她精心打理的西府海棠,却不肯让皱纹入画。
昨夜梦见老宅的八仙桌。母亲在剥新摘的蚕豆,青碧的豆荚裂开时发出“冰青色琴音”。我隔着三十年光阴望她,忽觉宋词里的晓风残月原是有温度的——她抬头笑问“京城可有人替你裁春衫”时,一粒豆子滚落桌底,叮咚声惊破满室寂静,原来“便纵有千种风情,更与何人说”。
今天回到北京的家里,背包里有一个母亲偷塞进来的包裹。包裹里好几层袋子用红布扎着,里面是三大团被母亲挤干水分的酸菜丝。附的纸条上抄着工笔小楷:“莫问奈何奈何“,而我却偏偏知道下一句是”不忘千结泪织”。袋子夹层凝着水珠,恍惚是她年轻时在灶前煨汤的汗。我抱着这包深情的《雨霖铃》走在国贸桥下,看车流如汴河舟楫穿梭,终是懂得有些思念注定要隔着“杨柳岸”,在“酒醒何处”的诘问里,将彼此站成两阕押不同韵脚的词。
暮色四合时,我拍下楼下花园早开的迎春花发给母亲。她回复的语音带着笑:“花开得这样急,倒像怕赶不上什么似的。” 春风裹着戏腔掠过楼宇间的峡谷,恍惚听见八百年前那个白衣卿相在唱:“多情自古伤离别,更那堪,冷落清秋节”,而母亲正在故乡的梅子树下,把给我的回执写成下阕的“便纵有千种风情”。
更多热门说说阅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