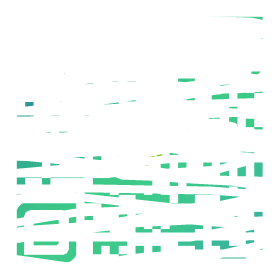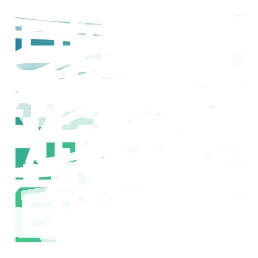好久没有给母亲打电话了。除了工作需要之外,是好久都不给人打电话了。晚上倒是会常常梦见母亲。比如昨晚。 一家人在田里干活,挖坑种菜,应该是种包菜,我们家最大的一块地,大概超过一亩半,全部要种上包菜,作为经济作物。累得直不起腰,索性就一直低头躬身,保持一个姿势机械地挥锄、甩土、放苗、埋土、抚平,再下一个坑。远远地,看见一群人围着母亲在争吵些什么。我有良好的家教,大人的事不准掺和,于是继续埋头苦干。姑姑们过去了,她们一起跟那群人争吵,她们吵着吵着就吵到我身边来了,我直不起腰,就听着她们讲:原来这是一群来逼债的,母亲欠了3000块钱呢,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,母亲打死不肯交钱,姑姑们也说交不起,家里没有钱。 农村人赖账就一条:我没有钱,我家里什么也没有,只有米缸里还有半斗米,你要就拿去。 可是母亲怎么会欠债呢?工商局的说,她有一年违章摆卖,没交罚金,只收了罚单,一晃二十年过去了,罚单利滚利,累积起来就高达三千块了。 那些人挎着公文包,人模狗样,气势汹汹地逼着母亲交钱,并威胁说当年那些在路边摆卖的人都交钱了,只有你不交,不交钱,会影响你全家人的征信度,以后你们家想要办什么事都会受影响。 父亲是不怕的。可母亲肯定怕,我也在想,要不就替母亲交了罚款吧,可姑姑们不让,姑姑们说,那些年我们老百姓穷成啥样了,缺吃短穿的,好不容易从牙缝里挤出一点来卖了换个看病钱,还要交税,交罚单,没天理呀! 那些年,每到除夕就有人来家里催债,他们挎着公文包💼,穿着城里人才有的正装,威风凛凛。当然是来催父亲的,父亲淡定地跟他们谈判,坐在厅里木沙发上,男人们的谈话郑重其事,女人和孩子屏息敛声,远远地看着不敢打扰,只偶尔进去添个茶。看得出来,父亲总是在找话题缓和严肃紧张的氛围,从来不让谈话变得剑拔弩张,对方声音高的时候,父亲便不说话,慢条斯理地抽烟🚬,轻轻地弹一弹烟灰。烟雾缭绕的过程有时候特别漫长,有时候能听见笑声。那是父亲的难关,父亲总是能挺过去的。父亲说:别把人逼急了,大不了同归于尽,弄一包炸药,大家一起都变作土。父亲那样子,一定是说到做到的,他在外面承接路桥工程的时候是可以买到炸药炸土石的,那些炸药同时也能炸房子。 父亲从来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,他是孤儿,流浪到我家,贱命一条,要就拿去。母亲却总是怕这怕那,一遇事就心肝砰砰跳,心慌心悸好几天,感觉天要塌了,还没人顶着。母亲顶不住压力的时候就会离家出走,我清楚地记得,大年三十晚上,我们姐弟几个哭着到处找妈妈,田埂上,马路上,后来惊动了全村人,大家打着手电帮我们找妈妈,那一年好冷啊,母亲被找回来之后在被窝里躺了好几天。

评论:
在晓风残月里周而复始: 后来呢?怎么样了啊?
作者: 后来我们就长大了,母亲就变老了[呲牙笑]
在晓风残月里周而复始: [捂脸哭][玫瑰][玫瑰][玫瑰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