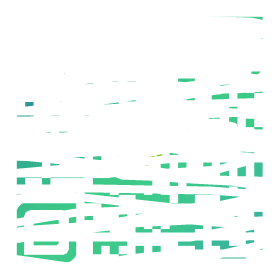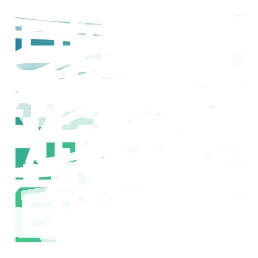崔叔走後的余痛還在。倒也不是多麼的情深義重,只是那樣一個鮮活的一起喝酒吃肉說走就走的朋友,毫無預兆的驟然離世,是一個時代的終結,慢慢接受一場場不可回避的作別。 在心口上刺了朵吳冠中風格的玫瑰,特別特別痛。成都返渝的動車上給發小分享那刻的體悟,沒有回復。隔天再發,沒有回復。第三日電話,依舊沒有回復。聯繫家人才得知,彼時剛下手術台,正在ICU觀察,也無法探視。 那晚睡得極淺,害怕像之前一樣,睡前一切正常,睜眼人已離去。 萬幸,基本是平安的。 只是身體里多了器械,每天要吃許多種藥,一個月過去了,依舊虛弱得不成樣子。 房子裝修開始收尾,色彩是大面積的白。 收拾去倫敦的行李,衣物是清一色的黑。 關於去留依舊沒得出結論。 走意味著一無所有,從頭來過,卻可能新生。 留意味著如今一切,僥倖擁有,卻慢慢衰減。 大概,答案依舊在路上。
评论:
卡妙🐈⬛: 十年前家里人住院,听到电话响心里默认是好消息马上就接起来;现在家里人住院,但凡听到电话响都要先深呼吸自己做个心理建设再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