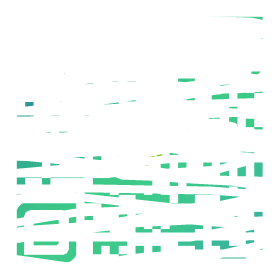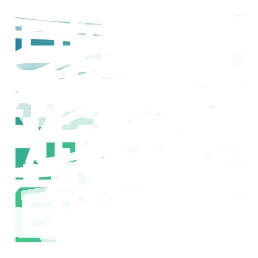《山魂》 Hubery 纪念死去的爷爷,享年80岁 黔岭的雾总在黎明前漫过老屋的檐角。爷爷的狼毫在宣纸上洇开墨色时,我常疑心那些苍劲的笔画是山岚凝成的魂魄。他的手腕悬垂如苍松,墨迹游走间,仿佛能听见六十年前猎枪擦过马尾松的簌响。 悬壶的手,原该沾着药香。可这只手分明能折弯竹篾编出会唱歌的雀笼,能在铁锅里翻炒出七月的辣香。山民们捧着新打的野味来换药方时,他的银针总在月光下泛着慈悲的寒芒。记得那个雪夜,后山产妇的血气惊醒了整个寨子。爷爷背起药箱踩碎冰凌,蓑衣在风雪中翻飞成白鹇的尾羽。后来产妇家的腊肉挂满檐下,他却在火塘边雕起了竹根,说医者本是山神的使徒。 猎枪是他丈量天地的戒尺。当商队的马蹄声还在石板路上叮当,他已卸下算盘,把火药装进鹿皮囊。我十岁那年跟着他钻进箭竹林,看晨露在他猎刀上凝成水晶。斑鸠惊起的刹那,他教我辨认风中残留的羽音:"枪响不是终结,是山神收回了借给生灵的时光。"暮色里拾回的野兔,总被他悄悄放进孤寡老人的柴扉。 老屋阁楼至今悬着那张柘木弓。松烟墨与当归的气息在梁间缠绵,竹筛漏下的光斑里,我总看见他给邻家小儿推拿时颤动的银须。当他最后一次进山,猎枪里装的竟是给野蜂治病的艾草。有人说他化作了林间的风,有人说他成了某座雪峰的轮廓。我只知道,每当我用他教的指法揉开婴儿的啼哭,墨池里就荡开一圈新的年轮。 那些他救治过的生命,那些他放归山野的生灵,此刻正在贵州十万大山里,替他呼吸着自由的空气。
评论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