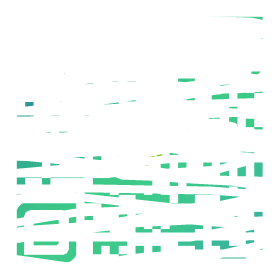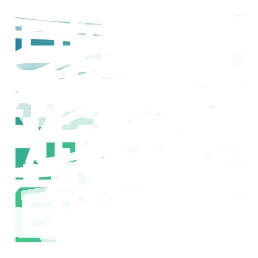那年的木兰花谢得比往常早。阿蒂克斯说,知更鸟总是在最安静的清晨死去,它们的翅膀掠过纱窗,羽毛上沾着露水,像一片被风吹落的雪。那时我不懂死亡,就像我不懂为何芬奇家的信箱总在春天生锈——直到昨夜电话铃响,电流声里传来大洋彼岸的潮湿叹息。 梅科姆镇的人都知道,知更鸟不该被杀死。它们把巢筑在法院广场的橡树上,用歌声丈量晨昏。可没人告诉过我,有些鸟儿注定要飞向永恒的暮色。她曾穿着缀满亮片的演出服站在镁光灯下,笑声像六月蝉鸣般清亮,如今却成了杰姆望远镜里一颗黯去的星。 我站在廊檐下剥橘子,汁液渗进指纹的沟壑。卡波妮总说橘子皮能驱邪,可那些细小的油腺终究没能拦住什么。玄关镜框里的结婚照开始泛黄,她耳畔的珍珠依然白得刺眼,像月光凝结的霜。杰姆问照片里的笑容为什么和现在不同,我往威士忌里加了三块冰。 镇上的流言比棉絮还轻。杜博斯太太摇着轮椅经过栅栏,说台北的雨会淋湿佛罗里达的沙地。亚历山德拉姑姑往红茶里多加了一匙糖,瓷勺碰着杯壁叮咚作响:“血统高贵的淑女不该被摄像机追逐。”可我记得她光脚踩在沙滩上的样子,脚踝缠着贝壳串成的链子,浪花把婚纱染成雾蓝色。 莫迪小姐的火炉烤着栗子,甜香漫过矮墙。“它们裂开时总在深夜,”她往我手心放了两颗温热的果实,“就像有些人的心。”壁炉架上摆着去年圣诞的合影,她的红围巾像一道未愈合的伤口。 警长泰勒深夜敲开家门,说摄影棚的聚光灯太烫,烧穿了知更鸟的喉咙。我想起她最后一次吻别时睫毛的颤动,像蝴蝶停驻在即将闭合的圣经上。杰姆的望远镜从阁楼跌落,镜片碎成十二片锋利的月亮。 阿蒂克斯的怀表停在九点十七分。他说正义是件白衬衫,可没人告诉我眼泪会让它发黄。我蹲在门廊擦皮鞋,鞋油染黑了半个黎明。远处的橡树沙沙作响,仿佛有透明的翅膀掠过树梢。 卡波妮把早餐煎饼摆成心形,枫糖浆在边缘凝固成琥珀色的痂。“死亡会让某些人变得更真实。”她说这话时教堂钟声正响,惊起满院的鸽子。我数着羽毛落下的次数,直到数字大过我们共度的春秋。 梅科姆镇的春天来得悄无声息。木兰花苞在雨夜里胀裂,像无数未说出口的誓言。杰姆把知更鸟的羽毛夹进词典,停在"eternity"那一页。我翻开她留下的剧本,空白处画着歪斜的爱心,墨迹晕开成台北的雨季。 阿蒂克斯终于修好了信箱。新刷的绿漆盖住锈痕,可铰链的吱呀声总在午夜响起。我想起她教我用中文说“永远”,音节在舌尖打转,最终坠入墨西哥湾咸涩的风里。 今夜又有知更鸟在歌唱。月光把它们的影子投在窗帘上,像一串正在消散的省略号。


评论: